2025年07月18日 王小柔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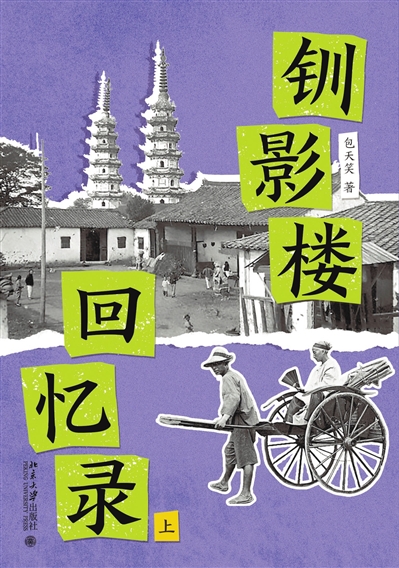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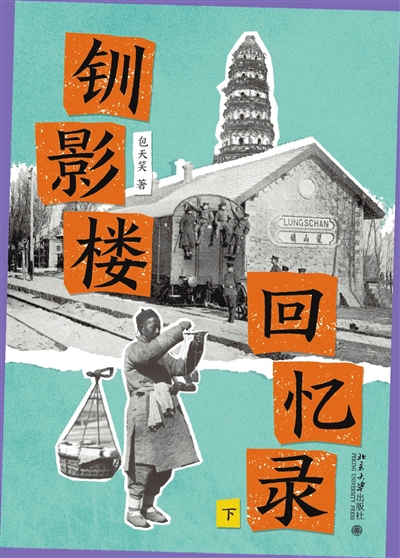 《钏影楼回忆录》,包天笑著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5年6月。
《钏影楼回忆录》,包天笑著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25年6月。
包天笑的笔触在时光的石板上凿刻出清末民初的众生相。《钏影楼回忆录》并非简单的往事堆砌,而是一幅用墨痕织就的时代织锦,在报馆的铅字与译书处的油灯之间,在张园的茶盏与石库门的弄堂深处,藏着一个王朝覆灭与新生的故事。当这位民国通俗文坛盟主以暮年之眼回望此生,那些被岁月尘封的细节在纸上复活,化作旧上海的烟雨。
铅字里的江湖
上海的小报世界在包天笑的笔下如同一个光怪陆离的江湖,而李伯元的《游戏报》则是这个江湖的一面杏黄旗。当1897年的报童们在石库门弄堂里高喊《游戏报》“要哦”时,那些被大报拒之门外的“街谈巷议”便找到了栖身之所。包天笑记得,这些巴掌大的报纸“只有大报纸张之半”,却装下了比大报更汹涌的世态炎凉,因为从官场到伶界,从粉墨春秋到奇闻逸事,无不在小报的方寸之间上演。
《晶报》的崛起堪称小报史上的一场革命。当余大雄将三日刊的附张从《神州日报》剥离时,三个“日”字拼成的“晶”字不仅象征着“光明清澈”,更暗含着对大报的挑战。包天笑以亲历者的视角还原了这份小报的生存智慧:余大雄带着“徽骆驼”的韧劲,以“脚编辑”的身份穿梭于律师、医师与寓公等之间,将大报“不敢登、不便登、不屑登”的猛料变成头版头条。
在《晶报》的编辑室里,包天笑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鲜活的新闻生产场景。张丹斧的怪文与余大雄的谋略在此碰撞,律师的秘闻与名医的珍闻在此发酵,甚至朋友带来的朋友的闲聊都可能变成第二天的铅字文。这种没有“内勤外勤”、不支付“薪资稿费”的新闻采集方式,却催生了最具杀伤力的报道:当德国医生希米脱的“返老还童术”吹得天花乱坠时,《晶报》刊登的《圣殿记》以“康圣人臀部打针”的幽默讽刺,惹来一场轰动沪上的官司。包天笑记得,当英国领事判决余大雄赔偿一元时,希米脱怒吼着离场,而《晶报》的销量却暴涨千份——这一元钱的判决,恰似旧上海中西法律博弈的一个隐喻,在殖民者的司法体系下,小报以近乎荒诞的方式赢得了道义的胜利。
小报与大报的博弈不仅在内容,更在形态与生存哲学。包天笑敏锐地指出,大报“靠广告,广告越多,纸张就越多”,而小报“靠发行,往往仅有半张的纸,却能与大报数张纸的价目并驾齐驱”。这种“短兵相接”的生存智慧,从《晶报》对副刊的影响中可见一斑。当《申报》的《自由谈》、《新闻报》的《快活林》吸收小报的“精华”时,那些曾经被鄙夷的“街谈巷议”便堂而皇之地登上了大报的版面,完成了从江湖草莽到庙堂雅音的蜕变。在包天笑的叙述中,小报的兴衰不仅是报业的变迁,更是一个时代价值观念的流转,从李伯元笔下的官场谴责到余大雄手中的社会爆料,小报始终是旧上海的一面哈哈镜,照见的不仅是洋场才子的风流,更是一个王朝瓦解时的众生相。
金粟斋里的文化突围
在南京路西北的登贤里,包天笑与一群维新志士在石库门里点燃了文化启蒙的灯火。金粟斋译书处的迁移史,恰似一部晚清知识分子的流亡图谱。从繁华的大马路迁到新建的白克路(后称凤阳路),从野鸡堂子的喧嚣旁搬到吴彦复与章太炎的隔壁,这个三上三下的石库门房子,成了“戊戌政变”后新思想的孵化器。包天笑记得,围墙尚未砌就,只用篱笆围着,邻居是一片荒冢乱草,却不妨碍译书处的煤油灯夜夜通明,将西方的思想火种一点点译介到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。
译书处的日常充满了新旧杂陈的趣味,包天笑捕捉到了那个时代最具张力的文化景观。章太炎为他写的名片必用“黄帝纪元”,字里行间透着对清朝的不屑;而吴彦复家的餐桌上,常常坐满了从日本、欧美回国的青年,章行严(章士钊)则与太炎先生讨论学术,这样的场景,恰是新旧思想交锋的具象化。
金粟斋的高光时刻,是严复的名学讲演会。当这位留着浓黑小胡子、眼镜用黑丝线缚住的翻译家站在半桌前时,包天笑看到了新旧文化的奇妙碰撞:严复常常夹杂了英文的演讲,让不懂英文的人如坠云雾,而他脚边的水烟袋又时时冒出传统士大夫的习气。这场名为“名学”(逻辑学)的讲演,在当时的上海堪称先锋之举。
译书处与《中外日报》的合作,构成了晚清文化传播的双轨制。包天笑往返于报馆与译书处之间,看到了两种文化载体的共生关系:金粟斋的译著在《中外日报》登广告,报馆又代售书籍,形成了“译—刊—售”的完整链条。在汪颂阁的主笔房里,翻译先生们对着《字林西报》与日本报纸苦思冥想,因为“各国的通讯社都没有到上海来,只有英国的路透社一家,取价甚昂”。这种信息获取的艰难,更显出金粟斋译书的价值——当叶浩吾译日文、温宗尧译西文时,他们手中的笔不仅是翻译工具,更是刺破信息茧房的利器。
在登贤里的隔壁,薛锦琴女士的出现如同一道闪电。当这位十八九岁的广东女子在张园的演说台上“侃侃而谈,说得非常慷慨激昂”时,包天笑记录下了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瞬间:“一双天足,穿了那种大脚管裤子,背后拖了一条大辫子”。天足与辫子的并存,恰是新旧交替时代的生动写照。更富戏剧性的是,吴彦复让两位女儿拜薛锦琴为师,长女吴弱男后来竟嫁给了常来译书处的章行严。这种姻缘的巧合,在包天笑的笔下不再是八卦,而是文化交融的隐喻。金粟斋的灯火虽然微弱,却照亮了一代人的文化突围之路,从译介西学到倡导女学,从讨论名学到谋划革命,这个石库门里的小天地,恰是大时代变革的微缩景观。
旧时光里的性情中人
在包天笑的记忆相册里,清末民初的文人们以鲜活的姿态走来,每个人的身上都带着时代的印记。章太炎的“鸭屁股”发型与团扇是最醒目的标志,这位余杭学者“排满思想已塞满他的脑子里,但讲话还是那样温文迟缓”,用一口难懂的“余杭国语”谈古论今。包天笑记得,有人请他写扇子,他必用古艳的字体书写,而自己求写的名片,也成了案头的珍藏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严复,他的金丝眼镜断了一脚,用黑丝线缚住,“虽为高级官僚,却有一种落拓名士派头”,在名学讲演会上,他站着讲了一小时,“平心静气,还说了许多谦逊话”,这种反差让包天笑看到了知识分子在新旧之间的挣扎。
马君武的痴与执最是动人。包天笑常见他“坐在人力车上,尚手不释卷咿唔不绝”,而他让母、夫人入女学的举动更成了朋友间的趣谈。“母云:‘我已五十许人了,何能再求学?’但君武固请,至于跪求”,最终太夫人“梳辫子作女学生妆,随少女曾入学数星期”。这种近乎偏执的劝学,在包天笑看来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心态:一面是对旧礼教的叛逆,一面是对新思想的痴狂。
吴彦复的家是文人雅集的舞台。这位“礼贤好客”的公子,家中常常“高朋满座,议论风生”,章太炎在此寄居,沈翔云、马君武、林万里等青年才俊在此会聚。包天笑记得,彦复送他一部《北山诗集》,他回赠再版的《迦茵小传》,竟引得彦复作诗相和:“万书堆里垂垂老,悔向人来说古今。”后来读梁启超的《饮冰室诗话》,才知此诗背后藏着彦复如夫人彭嫣“下堂求去”的隐痛。包天笑的叙述从不刻意渲染,却于细节处见真章。当彦复的女儿吴弱男嫁给章行严后,包天笑在北京车站偶遇已是章夫人的弱男,“那时行严在沪大病,恰巧邵飘萍来车站送我,邻室的章夫人,还托邵君打电报到上海去”,这种时空交错的重逢,让当年登贤里的青年才俊成为时代的主角,而包天笑的记忆则成了连接过去与现在的纽带。
邱公恪与吴孟班的悲剧是文人命运的缩影。这对“青年伉俪,情好素笃”,却在短短数年间相继离世,“两人年均未届三十”。包天笑记得,公恪赴日习陆军,“但日本的那种军官学校,课务严厉,他虽意气飞扬,但体魄不能强固如北方健儿”,加上夫人难产而逝,最终抑郁成疾。叶浩吾的挽联“中国少年死,知己一人亡”与蒋观云的诗句“女权撒手心犹热,一样销魂是国殇”,将个人的悲剧升华为时代的挽歌。在包天笑的笔下,这些早逝的文人不是历史的注脚,而是活生生的生命,他们的理想与幻灭,恰是那代人精神困境的写照。
胡适之的冶游被《晶报》曝光的场景,则透着文人的狡黠与时代的宽容。当“胡博士”从北京来沪,即将出国时,被同乡余大雄撞见“在某处吃花酒”,这位“中国教育界的名人”的风流韵事立刻成了小报的头条。包天笑没有苛责,反而以略带调侃的笔触记录下这一“大报所不便登而不屑登”的新闻,仿佛在说:即便是新思想的倡导者,也难脱旧上海的风月场。这种宽容的笔触,让文人的形象更加立体。他们不是高不可攀的圣贤,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人,在新旧道德的夹缝中,既想引领时代,又难舍人间烟火。
石库门里的微观叙事
包天笑的回忆录如同一把钥匙,打开了旧上海的记忆密室。在他的笔下,城市的变迁不是宏大的叙事,而是具体到每条马路、每座建筑的微观记忆。从南京路的“大马路”到白克路的“新马路”,从张园的安垲第到登贤里的石库门,这些地理坐标不仅是空间的标识,更是时代的刻度。当包天笑说“那条马路在南京路的西北,当时还未定名,大家呼之为新马路,后来便定名为白克路,租界收回以后,又改名为凤阳路了”时,他实际上在记录一座城市身份认同的变迁,从殖民者的命名到主权回收后的更名,一条马路的历史恰是一座城市的殖民记忆。
张园是旧上海的公共空间样本。这座由张叔和(张鸿禄)用“宦囊”建造的花园,既是李伯元与包天笑晤面的场所,也是薛锦琴发表演说的舞台。包天笑记得,园内“有一厅,名安垲第,可容数百人”,当维新志士在此集会时,“一时鼓掌之声,有如雷动”。这种公共空间的形成,在包天笑看来意义非凡。它打破了传统士大夫的私密交往模式,让思想的交锋在开放的空间中进行,恰如园主人张叔和的命运,张园本身就是一个新旧交织的产物,在官僚资本与市民文化的碰撞中,催生出新型的城市公共生活。
石库门里的日常生活藏着城市的表情。包天笑描写金粟斋的迁移时,特别提到“后门相对的一家,便是吴彦复的家;在我们前面,有一片方场,另外有一带竹篱,便是薛锦琴女士的家”,这种邻里结构在旧上海非常典型——文人、志士、普通市民在同一弄堂里比邻而居,鸡犬相闻间,思想的火花便在不经意间碰撞。当包天笑看到章行严“携着吴彦复的两位女公子,到薛锦琴的家里去”拜师时,他记录的不仅是一次寻常的拜访,更是一种新型社会关系的形成——在石库门的有限空间里,不同背景的人打破了传统的阶层壁垒,构成了一个微型的现代社会雏形。
报馆与译书处的空间布局折射着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。《神州日报》的编辑室“既旧且窄”,“全编辑部只有吴瑞书一人包办”,而《晶报》的编辑室同时也是会客室,“有时少长咸集,群贤毕至,余大雄的朋友,张丹斧的朋友,朋友带来的朋友,如梁上之燕,自去自来”。这种空间的开放性,与金粟斋译书处的“三上三下石库门式”的结构形成对比——前者是市场化的新闻生产,后者是精英化的思想孵化,两种空间形态共同构成了旧上海的文化生态。包天笑特别注意到,《申报》想收购《晶报》时,“一部《神州日报》遗传下来的平版老爷车机器,一副断烂零落的铅字本”并不值钱,真正想买的是“《晶报》二字而已”,这种对品牌价值的认知,恰恰说明上海的报业已开始具备现代商业意识。
城市记忆在饮食、服饰等细节中流淌。薛锦琴的“大脚管裤子”与章太炎的“不古不今、不僧不俗的衣服”,构成了城市服饰的风景线,天足与辫子并存,和服与马褂同行,这种服饰的混搭恰是文化多元的象征。当包天笑说“那时没有穿西装的人,因为大家都拖着一条辫子”时,他实际上在记录一个微妙的过渡时刻:西装尚未普及,辫子仍未剪除,城市的服饰文化正处于新旧交替的阵痛期。
在《钏影楼回忆录》的字里行间,旧上海不是一个模糊的背景,而是有血有肉的主角。包天笑以报人特有的敏锐,从大马路的繁华到新马路的荒凉,从报馆的铅字到石库门的炊烟,以精准的视角捕捉到城市发展中的每个细节。当包天笑在钏影楼的昏黄灯光下搁笔时,那些沾着旧上海烟尘的记忆便永远封存在墨迹里。他笔下的铅字江湖、译书灯火、文人面影与石库门岁月,在历史的册页上留下深浅不一的痕迹。如今再看张园的安垲第早成尘埃,白克路的篱笆墙也换了新颜,唯有回忆录里章太炎的团扇、严复的断脚眼镜、马君武的人力车书影,仍在时光深处泛着微光,像老上海弄堂里未熄的灯,照着今天还在看这本书的读者。你会觉得,所有风云际会终成过眼云烟,唯有普通人在时代夹缝里的呼吸与心跳,才最真实。
